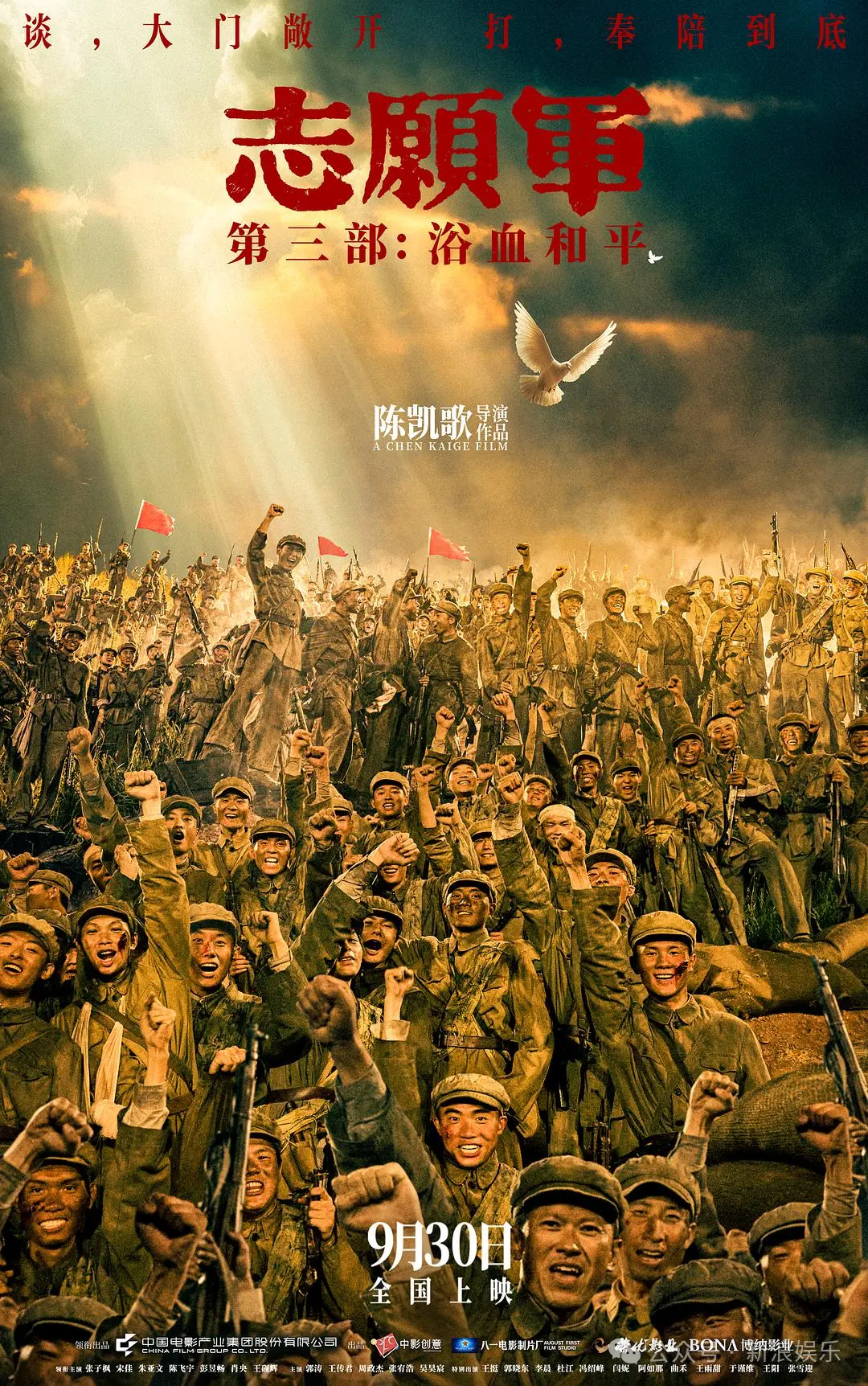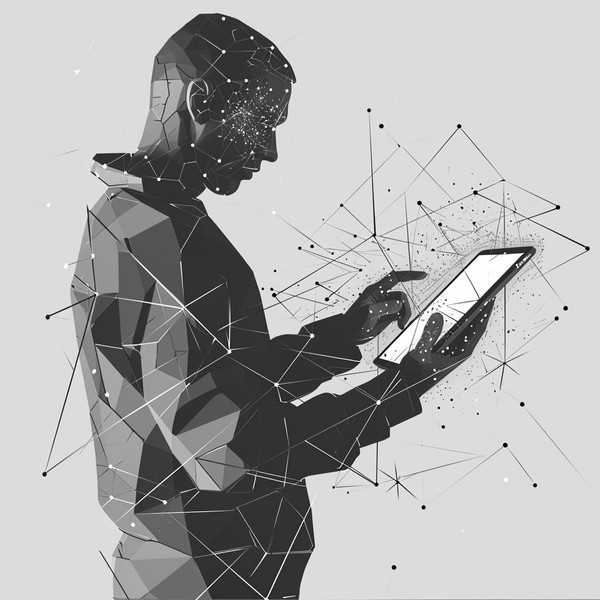 创盈配资
创盈配资
智能手机看似是我们心智的延伸,但它们通过操控用户注意力服务于企业利益,与传统认知工具大相径庭。更像寄生虫而非心智延伸。
智能手机究竟是我们心智的一部分,还是悄然寄生的外来者?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。支持“延伸心智论”(EMT)的学者认为,我们的认知能力早已突破大脑的界限,渗透到身体和外部世界中。例如,学龄前儿童用手指计算“2+3”,购物者依赖清单记住所需物品,拼字游戏玩家通过摆弄字母架探索可能的单词。这些外部资源与我们的心智紧密协作,成就了仅靠大脑无法完成的任务,因而被认为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。
智能手机似乎是这一理论的最佳例证。如今,这些小巧而强大的微型计算机几乎无处不在。我们将记忆电话号码、导航路线、甚至记录生活点滴的任务统统交给它们。试想,若没有智能手机,我们是否还能轻松找到陌生城市的某条街道?或者准确回忆朋友的生日?智能手机仿佛成了我们认知的“义肢”,随时可取、值得信赖创盈配资,就像奥托(Otto)那本记录记忆的笔记本,成了他因阿尔茨海默症衰退心智的可靠伙伴。
然而,这种直观的认知延伸观点忽略了智能手机的另一面。早期智能手机,如黑莓或掌上电脑,确实像电子版的电话簿或地图,单纯为用户服务。但今天的智能手机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它们内置的应用程序和算法被设计为捕获我们的注意力,以实现科技公司的商业目标。脸书的“点赞”按钮、推送通知,甚至社交媒体的滚动机制,都在利用心理学原理让我们沉迷其中。曾任脸书创始总裁的Sean Parker坦言,他们的目标是“尽可能多地消耗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”。这并非设备被恶意篡改的结果,而是其设计初衷。
试想一下,当你计划健身却在手机上“末日滚动”两小时,宝贵时间被无意义的新闻吞噬,这难道是你想要的结果吗?智能手机的这种行为与认知延伸的定义背道而驰。认知系统的一部分不应违背使用者的目标,就像身体的细胞通常合作以维持整体生存,而非各自为政。癌细胞因背叛整体被视为异常,而智能手机的“背叛”却是其核心功能之一。
因此,与其将智能手机视为心智的延伸,不如用生物学中的共生关系来理解。共生关系涵盖了从互利到寄生的各种互动。例如,清道夫鱼为大鱼清理寄生虫,自己获取食物,双方互利。而吸盘鱼依附鲨鱼获取残羹冷炙,对鲨鱼无害无益,属于单方受益的共生。寄生关系则不同,寄生虫以损害宿主为代价谋利。智能手机与我们的关系有时像清道夫鱼般互利,比如提供导航或即时通讯;但更多时候,它像寄生虫,诱导我们沉迷,消耗时间,收集数据以供商业操控,如剑桥分析事件所示。
这种关系的动态性尤为重要。生物共生关系并非一成不变,清道夫鱼偶尔会偷吃大鱼的鳞片,破坏平衡,但大鱼能通过驱逐或拒绝合作来惩罚。在智能手机的世界中,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博弈。用户可能因不满数据滥用而卸载应用,但现代社会对智能手机的依赖——从工作到社交——让退出成本高昂,仿佛我们与手机陷入了一种“强制性共生”。正如高度依赖的夫妻,彼此分担认知任务,但若一方背叛,退出关系可能代价巨大。
从共生视角看智能手机,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其双面性。它既是便利生活的工具,也可能成为剥削我们注意力的寄生者。这种分析不仅揭示了人与科技的复杂关系,还提醒我们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保持警惕。毕竟,寄生关系可能触发反制演化,就像人类文化通过集体记忆减轻个体大脑负担一样,未来的我们或许会发展出新的策略,与这些“心智寄生虫”抗衡。
本文译自 tandfonline创盈配资,由 BALI 编辑发布。
通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